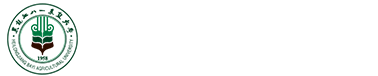論中國精神的辯證譜系
——基于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融合機理的探討
葉子犀
摘 要: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精神譜系的源頭,與中華民族精神、紅色基因、龍江精神等是內(nèi)涵與外延的關(guān)系。眾所周知,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是龍江優(yōu)秀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兩大精神融合機理研究為切入點,從哲學(xué)理論的高度闡釋龍江精神、紅色精神、中華民族精神的辯證關(guān)系,有助于深化對建黨精神的理解。
關(guān)鍵詞:建黨精神;中國精神;紅色精神;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哲學(xué)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首次闡釋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dān)當(dāng)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精神譜系的源頭,是中國精神的核心內(nèi)容和鮮明標識。可見,要深刻把握建黨精神的科學(xué)內(nèi)涵,需要梳理和論證中國精神、紅色精神、地域精神的有機聯(lián)系。
龍江精神是黑龍江地區(qū)紅色精神的顯著標識,作為龍江精神主要代表的四大精神主要有:東北抗聯(lián)精神、北大精神、大慶精神、鐵人精神。而僅大慶地區(qū)就涵蓋了其中的三個精神。研究各大精神的融合機理,無論對于傳承和弘揚龍江精神,還是對于把握紅色精神、中國精神、建黨精神的整體脈絡(luò),對于弘揚光榮革命傳統(tǒng)、傳承紅色血脈,都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本文從探索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的融合機理著手,在“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的哲學(xué)視野和框架內(nèi),借助分析“部分作為整體中的部分、整體作為部分中的整體”的辯證法思想,進而闡明中國精神、紅色精神、龍江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的有機聯(lián)系。
一、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基本情況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也強調(diào),要鞏固全體人民團結(jié)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chǔ),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tài)化、制度化,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可見,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是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之義和重要舉措。
作為中華民族精神重要組成部分的龍江精神,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紅色基因傳承。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東北抗聯(lián)精神是龍江優(yōu)秀精神的主要代表。其中,大慶地區(qū)就包含和融匯了其中的三大精神,而鐵人精神又直接脫胎于大慶精神當(dāng)中。因此,就大慶地區(qū)而言,大慶精神和北大荒精神是該地區(qū)傳承和弘揚紅色基因和龍江精神的核心樞紐。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弘揚和傳承紅色基因、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浪潮中,在順應(yīng)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新形勢下,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不斷豐富自身的內(nèi)涵,相關(guān)的理論解讀和傳承、弘揚的實踐方式也開啟了新方向,展現(xiàn)出新的面貌。從前“獨立成型”“各自發(fā)展”的兩大精神,因地緣關(guān)系,逐漸呈現(xiàn)出齊頭并進、相互融合、共同發(fā)展的現(xiàn)實樣態(tài)。在大慶區(qū)域經(jīng)濟社會一體化發(fā)展的進程中,探索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一體化發(fā)展的有效機制,成為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研究主題。
(一)北大荒精神內(nèi)涵和發(fā)展現(xiàn)狀
1947年,毛澤東做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jù)地”的偉大號召,由此拉開了北大荒開發(fā)建設(shè)的序幕。經(jīng)過半個世紀開發(fā)建設(shè),北大荒歷經(jīng)“創(chuàng)建開發(fā)初期”(1947—1955)、“建設(shè)發(fā)展時期”(1956—1966)、“曲折發(fā)展時期”(1967—1978)、“改革開放時期”(1979—2000年)、“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發(fā)展時期”(2001至今)幾個發(fā)展階段,已經(jīng)建設(shè)成為現(xiàn)代化大農(nóng)業(yè)的國家商品糧基地和糧食安全戰(zhàn)略基地。
自解放以來,北大荒地域共經(jīng)歷了十?dāng)?shù)次移民文化的沖擊。上百萬的移民大軍給這片廣袤的黑土地帶來了生命活力。延安榮軍戰(zhàn)士、鐵道兵部隊等領(lǐng)銜的十萬軍墾隊伍,為北大荒帶來了延安精神,北大荒也從此留下了軍旅文化的烙印。此外,數(shù)萬支邊青年、五十多萬知識青年和數(shù)萬科技知識分子的紛紛到來,給北大荒帶來了豐富多彩、富有時代和青春氣息的知青文化。正是在以延安精神為代表的人民軍隊、支邊青年帶來的蓬勃青春、科技人員默默奉獻的無私精神,外來移民帶來的傳統(tǒng)美德等多重因素的交融下,最終凝結(jié)成“艱苦奮斗、勇于開拓、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北大荒精神。可見,北大荒精神是廣大官兵、支邊青年、科技人員、外來移民在改造自然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是特定歷史時期,在特定的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中誕生的。
可以說,北大荒精神的孕育,直接來源于墾荒部隊的軍旅文化、支邊知青文化,其源頭即紅色精神中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紅色基因是其核心,而軍旅文化、知青文化是其肥沃的土壤。綜上可知,北大荒精神的原初內(nèi)涵主要包含以下幾個環(huán)節(jié):
1.“艱苦奮斗”,凸顯的是拓荒者與惡劣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斗爭關(guān)系;
2.“勇于開拓”,意指在開荒拓土中開辟新天地、鉆研新技術(shù)、探索新方法、完善新管理;
3.“顧全大局”,意為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穩(wěn)定,尤其在洪水、地震、非典、禽流感等特殊災(zāi)害時期,北 大荒墾區(qū)向各受災(zāi)地區(qū)及時輸送糧食,為國家民族穩(wěn)定大局發(fā)揮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
4.“無私奉獻”,指特殊的革命建設(shè)時期,廣大官兵和支邊青年背井離鄉(xiāng),為祖國奉獻寶貴的青春和熱血。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黑龍江墾區(qū)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北大荒精神的內(nèi)涵也隨著時代的變革不斷豐富發(fā)展。過去的北大荒,當(dāng)?shù)厝嗣竦纳钪黝}是與天斗、與地斗,向地球開戰(zhàn),向荒原要糧;而進入新世紀,北大荒人民不再僅僅滿足于以“發(fā)展物質(zhì)生產(chǎn)、維系日常生活、強調(diào)糧食產(chǎn)出”為主要目的。墾區(qū)發(fā)展提出現(xiàn)代化大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目標,特別是隨著承載北大荒精神的黑龍江八一農(nóng)墾大學(xué)遷校至大慶以來,北大荒精神開始在大慶地區(qū)播撒種子,北大荒的現(xiàn)代化大農(nóng)業(yè)發(fā)展與大慶資源型城市轉(zhuǎn)型發(fā)展之間、北大荒文化建設(shè)與大慶油田文化建設(shè)之間、北大荒精神弘揚和傳承與大慶精神弘揚和傳承之間,出現(xiàn)了相互融通、同舟共濟、并肩前行的發(fā)展勢頭。
(二)大慶精神內(nèi)涵和發(fā)展現(xiàn)狀
大慶精神也是在艱難困苦的創(chuàng)業(yè)年代,為建設(shè)新中國、摘掉“貧油國”帽子的特殊時期應(yīng)運而生的。形成于石油會戰(zhàn)特定歷史時期的大慶精神,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承襲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不斷吸取新的實踐經(jīng)驗,獲得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fā)展。在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實踐中,大慶精神一方面保留了“愛國、創(chuàng)業(yè)、求實、奉獻”的基本內(nèi)涵;另一方面在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又不斷增添新內(nèi)涵。
1981年,國家經(jīng)委黨組《關(guān)于工業(yè)學(xué)大慶問題的報告》中,第一次完成對大慶精神“愛國、創(chuàng)業(yè)、求實、奉獻”內(nèi)涵的精準概括。1990 年,江澤民同志進一步將大慶精神基本內(nèi)涵拓展為“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創(chuàng)業(yè)精神;講究科學(xué)、“三老四嚴”的求實精神;胸懷全局、為國分憂的奉獻精神”。2000年,大慶油田有限責(zé)任公司深化對大慶精神的理解,從自身角度的得出了大慶精神的新世紀解讀——“發(fā)揚維護國家石油安全的愛國精神;發(fā)揚謀求企業(yè)百年成長的艱苦創(chuàng)業(yè)精神;發(fā)揚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求真務(wù)實精神;服務(wù)國家改革穩(wěn)定大局的奉獻精神”。2019年,為落實習(xí)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考察黑龍江重要指示和推進東北振興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加快推進大慶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爭當(dāng)全國資源型城市轉(zhuǎn)型發(fā)展排頭兵,中國共產(chǎn)黨大慶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關(guān)于深入挖掘和踐行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新的時代內(nèi)涵的決定》,對大慶精神的時代內(nèi)涵做了更深入的挖掘,提出“六十四字”新內(nèi)涵,在原有大慶精神語境下,最終將新的時代內(nèi)涵確定為:“政治堅定、對黨忠誠”“高揚旗幟、引領(lǐng)振興”“全面系統(tǒng)、開放包容”“改革創(chuàng)新、攻堅啃硬”“尊重規(guī)律、崇尚實干”“嚴謹精細、術(shù)業(yè)專攻”“勤勉敬業(yè)、真摯為民”“淡泊名利、清正廉潔”等六十四個字[1]2-3。
(三)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相關(guān)研究的基本情況
在新時期,關(guān)于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的凝練、概括和研究,以及傳承和弘揚,主要由黑龍江八一農(nóng)墾大學(xué)、東北石油大學(xué)、大慶師范學(xué)院等幾所當(dāng)?shù)馗咝R约按髴c市委黨校展開,相關(guān)理論研究和探索,在依托大慶精神研究基地、北大荒精神學(xué)術(shù)交流基地以及相關(guān)科普基地、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研究所、北大荒精神與文化研究所、以及相關(guān)思政課研修場館基礎(chǔ)上,以教科研人員的科研項目、論文等形式展開探索和論證。
截至2020年底,以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為題的期刊論文、會議、報紙等研究共計4261篇;以北大荒精神為題的研究共計956篇。研究充分結(jié)合不同的學(xué)科和專業(yè)方向,從兩大精神的歷史發(fā)展源流、新時代的內(nèi)涵、弘揚和傳承方式進行闡述,取得了豐碩成果。
二、兩大精神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的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shè)背景下,作為龍江優(yōu)秀精神的杰出代表,同時作為大慶市優(yōu)秀精神資源和紅色基因,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逐漸形成獨特的、具有地標性的精神風(fēng)貌、價值取向和高尚情操。在振興龍江發(fā)展和大慶市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的潮流中,二者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有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當(dāng)前,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研究尚存在以下問題:
1.兩大精神研究各自獨立發(fā)展,尚未形成區(qū)域性合力。
精神的孕育來自身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北大荒精神而言,它脫胎于現(xiàn)代化大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實際需要,植根于農(nóng)墾地區(qū)特殊的地域文化。因此有關(guān)北大荒精神的研究,在新世紀前后,主要圍繞著“北大荒文化”這一北大荒精神沃土的研究,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有反映開發(fā)建設(shè)特殊時期的北大荒知青文學(xué)、北大荒版畫、北大荒詩歌、北大荒影視劇作品,以及系列紀實作品等;進入新世紀后,有《北大荒全書》等代表性著作,分別從北大荒社會事業(yè)、北大荒政法軍事、北大荒商務(wù)、北大荒工業(yè)、北大荒文學(xué)藝術(shù)、北大荒大事記、北大荒簡史、北大荒農(nóng)業(yè)、北大荒英模、北大荒攝影等十個大方面相近凝練北大荒文化的內(nèi)涵。此外,進入新世紀以后,黑龍江省農(nóng)墾總局在“艱苦奮斗、勇于開拓、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北大荒精神十六個字內(nèi)涵基礎(chǔ)上,提煉出“誠信、務(wù)實、創(chuàng)新、卓越”的北大荒精神核心價值觀。
就大慶精神以及作為其特殊典型的鐵人精神而言,二者也植根于大慶石油會戰(zhàn)的特殊歷史時期。大慶石油會戰(zhàn)翻開了中國石油開發(fā)史上具有歷史轉(zhuǎn)折的一頁,由此開始了中國石油工業(yè)的跨越式發(fā)展。
大慶油田在創(chuàng)造巨大物質(zhì)財富的同時,鑄就了以“愛國、創(chuàng)業(yè)、求實、奉獻”為主要內(nèi)涵的大慶精神。同時,在毛主席“兩點論”“兩分法”哲學(xué)思想的指導(dǎo)下,實現(xiàn)了從鉆研鉆井技術(shù)、到實現(xiàn)科技創(chuàng)新、再到把井打到國外去的多次飛躍,從第一代鐵人王進喜開始,在生產(chǎn)建設(shè)的數(shù)十年中,大慶精神通過一個個具有特殊典型的“鐵人”精神得到凸顯和呈現(xiàn)。而“鐵人”身上折射出的鐵人精神的內(nèi)涵,都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艱苦奮斗精神、科學(xué)求實精神、奉獻精神等等優(yōu)秀品質(zhì)。大慶精神經(jīng)由鐵人精神的傳承,出現(xiàn)從第一代鐵人王進喜、第二代鐵人王啟民再到第三代鐵人李新民的典型人物及其事跡的口述史、作品和相關(guān)報道,從中不斷拓展出順應(yīng)時代發(fā)展的新內(nèi)涵。
可見,無論北大荒精神還是大慶精神,都是植根于特殊的地域,在特殊的生產(chǎn)生活中涌現(xiàn)的優(yōu)秀精神。兩大精神的出現(xiàn)具有大的共同的時代背景,即建國初期國家的生產(chǎn)建設(shè)時期,但二者又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并且受到“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和“石油工業(yè)”兩個不同行業(yè)領(lǐng)域的制約,有關(guān)二者的研究都局限在各自領(lǐng)域,這是由一定的地域背景、行業(yè)的特殊性決定的。但隨著黑龍江八一農(nóng)墾大學(xué)的遷校大慶,使得大慶市產(chǎn)生了市校融合發(fā)展的實際需求,兩大精神亟需融合一體,共同推動大慶市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
2.兩大精神研究停留在思想意識表層,尚缺少哲學(xué)理論統(tǒng)攝的高度、深度和廣度
國內(nèi)將北大荒精神與大慶精神進行比較,同時探討二者相結(jié)合的理論研究較少。目前少數(shù)論文,從若干方面嘗試著融合兩大精神的,主要體現(xiàn)在:
(1)將兩大精神溯源于延安精神,從對延安精神的先進性、開拓新、無私性的繼承和發(fā)揚角度,闡述二者具有同根同源性[2],但沒有繼續(xù)拓展同源的本質(zhì),以及每種精神內(nèi)在的特殊性,以及二者相互融合的當(dāng)代機制。
(2)從弘揚“闖關(guān)東精神、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大興安嶺精神和龍江交通精神”(簡稱“六大精神”)作為建設(shè)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提出要以“創(chuàng)業(yè)”為核心的內(nèi)涵的融合關(guān)鍵點,從“面向未來”的維度,以規(guī)避“溯源過去”出現(xiàn)的整合幾大精神出現(xiàn)的難題——①闖關(guān)東精神不為黑龍江獨有;②大慶精神與鐵人精神之間是并列關(guān)系還是互含關(guān)系;③北大荒、大慶、大興安嶺為地域劃分,龍江交通為行業(yè)或部分劃分[3]。
(3)簡單梳理龍江四大精神的發(fā)展歷史,以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視察和重要講話為線索,列舉一些先進典型作為范例。
(4)梳理了民族精神、中國精神、紅色精神的邏輯關(guān)系,從宏觀上對中華民族自革命和建設(shè)時期以來幾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其優(yōu)點在于全面而豐富,缺點在于受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對大慶精神、北大荒精神進行系統(tǒng)性發(fā)揮,以及從哲學(xué)學(xué)理上,對各精神的有機聯(lián)系進行的再深入的解讀[4]。
(5)具體闡述了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與民族精神、中國精神的內(nèi)涵和聯(lián)系,以及二者相互融合的時代需求,但仍局限在具體的內(nèi)涵領(lǐng)域,未上升到哲學(xué)高度做統(tǒng)一的概括和總結(jié)。
以上是兩大精神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以及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一起,可以歸結(jié)為一點,即“未形成系統(tǒng)性的理論構(gòu)架”,下面就該問題產(chǎn)生的根源進行分析。
(二)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研究未形成有機聯(lián)系的問題原因分析
1.在新世紀以前,早期的兩大精神研究受限于特定地域,以及“現(xiàn)代化大農(nóng)業(yè)”和“石油工業(yè)”兩大行業(yè)領(lǐng)域的特殊性質(zhì),沒有融合發(fā)展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和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求。因此兩大精神研究抽象、孤立地發(fā)展,兩大精神的匯流和淵源追溯,只形成了紛然雜陳的材料匯總,即質(zhì)料因,沒有闡明二者相互聯(lián)系、持續(xù)發(fā)展共融的動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
2.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大慶資源型城市轉(zhuǎn)型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以及順應(yīng)“龍江絲路帶”發(fā)展、“黑龍江農(nóng)墾體制綜合改革”等形勢和方針政策的提出,產(chǎn)生了兩大精神相互融合的機遇和挑戰(zhàn)。大慶市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市校融合發(fā)展,離不開兩大精神的引領(lǐng)和思想的指導(dǎo)作用。兩大精神合流的動力因和目的因自上而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兩大精神合流的理論闡述、融合的現(xiàn)實形式、傳承與弘揚的未來愿景和理念圖式,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3.近年來,不同理論在獨立的視角基礎(chǔ)上,從經(jīng)濟、社會、歷史、教育、文化、宣傳等等多個層面推動兩大精神的合流,作出了許多理論嘗試,但沒有依托統(tǒng)一的哲學(xué)理論框架內(nèi)做系統(tǒng)的梳理和闡發(fā)。因此存在三個方面的明顯缺陷:
一是在精神的傳承上,面對過去如何闡釋其內(nèi)涵的問題上,沒有把革命時期的紅色精神與建設(shè)時期的創(chuàng)新精神有機統(tǒng)一在一起;
二是沒有把特殊地域、特定行業(yè)的兩大精神統(tǒng)一到普遍的民族精神、時代精神、中國精神上來;
三是沒有闡明普遍的民族精神、中國精神與特殊的地域精神,以及典型的具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
總之,對于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內(nèi)涵的闡發(fā)和融合機制的闡述,不能僅僅局限在大慶地域,或黑龍江省地區(qū),而是需要同時在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當(dāng)中拓展其內(nèi)涵,并通過哲學(xué),特別是實踐哲學(xué)視野中闡述其融合的機制。
三、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融合機理的哲學(xué)透視
(一)以哲學(xué)為基本的理論視野
傳統(tǒng)哲學(xué)發(fā)展至今,每個時代都存在矛盾、對立及統(tǒng)一性的問題。矛盾對立的概念系統(tǒng),在古希臘時期體現(xiàn)表述為“一”與“多”的關(guān)系問題,在中世紀體現(xiàn)為“唯名”與“唯實”的關(guān)系問題,在近代體現(xiàn)為“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在現(xiàn)代更多體現(xiàn)為“存在者”與“存在”的關(guān)系問題。哲學(xué)問題體現(xiàn)在實踐領(lǐng)域,尤其是倫理學(xué)和政治學(xué)領(lǐng)域,主要表現(xiàn)為個人權(quán)利和國家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問題,可以用“個體性”和“普遍性”的對立范疇來標識。而我們運用哲學(xué)的辯證法思想,能讓“個體性”和“普遍性”之間的矛盾對立得以和解,形成有機統(tǒng)一。
(二)“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三一體的辯證關(guān)系
在哲學(xué)的視野中,一切事物都是具體的整體,它自身既具有內(nèi)在的目的因、發(fā)展的動力因,又有外顯的形式因,以及組成這一個體的質(zhì)料因。而因此從整全性來看,它是普遍性的完整整體,作為自身的表現(xiàn)方式,它又有自身發(fā)展的特殊表現(xiàn),而這種表現(xiàn)又是通過每個個體來完成和實現(xiàn)。因此,作為一個民族整體的民族精神,自身的本質(zhì)、外顯和完成,也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和“個體性”三個特征,三方面不是不同的三個事物或三種性質(zhì),而是同一事物的三種不同的表現(xiàn)。
1.民族精神、紅色精神、延安精神的辯證關(guān)系構(gòu)架
(1)民族精神的普遍性。2019年9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60周年賀信中強調(diào),“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充分表明,大慶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構(gòu)成單元和有機環(huán)節(jié)。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看來,特殊性是普遍性的構(gòu)成環(huán)節(jié)。首先,民族精神即是普遍性本身,但它并非一個抽象的、停留在自身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說,需將中華民族精神看作一個自身發(fā)展的、活生生的有機實體。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自我生長、自我超越、自我創(chuàng)新、自我完善和自身回復(fù)的理念。中華民族精神是一個具有自身歷史發(fā)展沿革,具有民族自我意識的普遍認同感,是每個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復(fù)興和肯定的總源頭,因此,它并不是一個抽象的主觀概念。僅就從主觀上看,它顯現(xiàn)為每個民族中的個人的普遍的民族自我意識;而從客觀上看,它還顯現(xiàn)為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機構(gòu)和組織、倫理關(guān)系以及國家形態(tài)。民族精神不單有共時性的維度,還具有時代精神的歷時性維度。
(2)紅色精神的特殊中介。作為民族精神貫穿始終的核心,則是愛國主義的紅色精神。從歷史分期來說,紅色精神經(jīng)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時期兩個階段:
一是新民主義革命時期的紅色精神的特殊性。紅色精神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孕育而生的,它包含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的“五四精神”,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初期的“紅船精神”,革命根據(jù)地初創(chuàng)時期形成的“井岡山精神”,中國革命處于低潮時期形成的“蘇區(qū)精神”,西北革命根據(jù)地創(chuàng)建時期形成的“渭華照金精神”,左右江革命根據(jù)地時期形成的“百色精神”,處在中國革命艱難困苦時期形成的“長征精神”,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鞏固時期形成的“延安精神”,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沂蒙山區(qū)形成的“沂蒙精神”,全國革命勝利時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
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時期的紅色精神的特殊性。抗美援朝戰(zhàn)爭孕育的“抗美援朝精神”,社會主義建設(shè)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北大荒精神”,社會主義建設(shè)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大慶精神”, 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產(chǎn)生的“雷鋒精神”,嚴重經(jīng)濟困難時期產(chǎn)生的“焦裕祿精神”,國民經(jīng)濟調(diào)整時期培育和形成的“紅旗渠精神”,社會主義建設(shè)高潮時期培育和形成的“兩彈一星精神”, 抗擊長江流域特大洪水災(zāi)害中孕育的“抗洪精神”, 改革開放新時期培育和形成的“載人航天精神”, 抗震救災(zāi)過程中形成的“抗震救災(zāi)精神”[4]。
(3)延安精神的個別體現(xiàn)。從上述梳理可知,延安精神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色精神這一特殊中介的個別顯現(xiàn)。首先,延安精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少數(shù)群體或八路軍三五九旅部隊特有的精神,而本身就是以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人民和軍隊具有的紅色革命精神在延安地區(qū)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因此它具有紅色精神的基因傳承,其次,它還是中華民族精神這一有機實體的反映和表現(xiàn),也是中華民族精神自身革命性、先進性、創(chuàng)新性、超越性的時代表現(xiàn)和縮影;再次,延安精神與紅色精神、中華民族精神是辯證統(tǒng)一、相互推論的同一,延安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中華民族精神是個體與整體的辯證關(guān)系,從哲學(xué)上講,就是個體性與整體性的關(guān)系,經(jīng)由“紅色精神”作為特殊的中介,使得個體與整體的關(guān)系透徹明晰。
2.中國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的有機統(tǒng)一
如前所述,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自身不是固定不變的僵化實體,而是具有內(nèi)在超越性、創(chuàng)新性和自我革命性的、自由自覺發(fā)展的倫理實體。中華民族精神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后,自身具有了更為先進和豐富的具體內(nèi)涵。因此,要將北大荒精神與大慶精神相互融合,需要在哲學(xué)視野中,重新理解和闡釋中華民族精神自身的變革和發(fā)展,只有站在民族精神自身發(fā)展的實體性高度上,才能真正把握兩大精神融合的有效機制和現(xiàn)實內(nèi)蘊。
(1)深刻把握 “中國精神”之為新時期民族精神的普遍性實體。
習(xí)近平總書記曾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實現(xiàn)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可見,中華民族精神在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當(dāng)代,用四個字來概括,就體現(xiàn)為“中國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精神普遍性的當(dāng)代詮釋。
(2)切實定位“延安精神”之為普遍性實體的特殊中介。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shè)新時期,面對國內(nèi)和國際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紛繁復(fù)雜的新形勢下,重提“延安精神”,其理論意義不僅是“認祖歸宗”的必要方式,亦或抵御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干擾、尤其是原子式個人自由主義文化滲透的外部需求,更是在哲學(xué)層面上透視“中國精神”這一普遍實體、傳承紅色基因、貫穿“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辯證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要求。“延安精神”是“紅色精神”在革命時期的表現(xiàn),也是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的共同血脈。1954年,原南泥灣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將軍,帶領(lǐng)鐵道兵開墾北大荒,將延安精神的種子播撒在北大荒大地上。1960年,中央軍委從部隊當(dāng)年退伍兵中動員三萬人,奔赴大慶新區(qū),幾萬人的會戰(zhàn)隊伍從此踏上了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征程,艱苦卓絕的石油大會戰(zhàn)就此打響。
可見,北大荒精神與大慶精神,同根同源,二者皆是“延安精神”的個別顯現(xiàn)。
(3)透徹理解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之為中國精神的個別體現(xiàn)。
進入新時期,大慶地區(qū)的兩大精神重新匯流,而作為中介的,正是以紅色精神為代表的延安精神。而這樣的追本溯源和中介,其目的恰恰是對于新時代中華民族精神——中國精神——這一根本實體的自由自覺地普遍認知和絕對認同。只有在對中國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慶精神這一“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三一體的辯證關(guān)系有了透徹理解,對三者關(guān)系視為同一實體的外化和特殊展開,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才能堅定個人的發(fā)展、個別地域的發(fā)展與民族精神實體的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的客觀事實。
四、結(jié)語
從哲學(xué)的辯證法立場來解讀中國精神、紅色精神、各歷史沿革的地域優(yōu)秀精神以及具有典型人物作為代表的精神,是新時期構(gòu)建中國精神及其分殊的理論嘗試,本文以黑龍江四大精神中的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鐵人精神作為切入點進行分析,提供了一種針對中國精神這一普遍性實體和不同層級的特殊性、個體性有機聯(lián)系的宏觀構(gòu)圖,有助于推動建黨精神的內(nèi)涵理解。
參考文獻:
[1]張俊等.大慶精神鐵人精神新的時代內(nèi)涵和踐行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9.第2-3頁
[2]蘇銳華.論黑龍江省三大精神對延安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J].奮斗,2010,(10).
[3]王愛麗.整合精神動力資源 再塑龍江文化之魂——我看“龍江精神”的建構(gòu)[J].學(xué)術(shù)交流,2012,(01).
[4]丁德科等.紅色精神百年史述論[J].渭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16,31(20).